张端鸿 同济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
日前,《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方案(2025—2027年)》出台,改革试点全面推进。这标志着我国高教体系即将进行系统性重塑,展现出国家推动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决心。然而,面对这一顶层设计,我们也应反思:为何高校自身难以主动完成结构优化,又为何学科专业的兴废总要依赖行政的“再安排”?
学科专业结构优化的必要性已经形成广泛共识,但也需要警惕“清仓式”改革。部分地方和高校将学科专业视作库存,集中撤并、粗暴压缩,追求短期整齐,却忽视了高等教育生态的复杂性与多样性。这种改革方式看似雷厉风行,实则可能在表面提高“效率”的背后,导致基础学科萎缩、文化断层和知识生态退化。
近年来,从“双一流”标准“自主确定”到学位授权点评估常态化,政策不断强调高校的能动性。但由于多数高校尚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教育组织,学科结构无法依靠内部机制进行优化与调整。专业设置往往取决于项目导向和审批逻辑,资源配置受限于财政结构,结构调整无法随社会演化自发完成。这也正是宏观政策需频频出手的根本原因。
在一个健康的高教生态中,学科和专业的设立与撤销应主要由学习者需求、社会反馈与学科自我更新所驱动。当某专业连续低迷,或某新兴领域快速兴起,学校应具备自我调整能力。但现实中,专业设点仍倚赖审批计划,退出机制乏力,使学科结构调整变为行政事项,而非教育组织的主动调适。学科的“存与废”成为政策引导事项而非内生判断结果。这不仅弱化了高校的教育自理能力,也让专业结构与现实需求之间始终存在错位。
很多人寄望于市场机制来调节学科专业结构,但必须看到,学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“市场主体”。从高考志愿填报到就业选择,从就业预期到城乡区域发展差异,学生常常在有限认知与路径依赖的平衡中作出一种“相对理性”的选择。“学生用脚投票”并不足以反映社会的真实需求,反而可能放大结构误导,自由选择也可能走向结构误导,令部分应保留的学科被误判为“无效资产”。
我们理解改革强调“服务国家战略”“对接新质生产力”背后的政策逻辑,但也必须警惕将“国家需要”过度简化为“热门学科排行榜”。高校若盲目追逐政策风口,可能引发新一轮学科趋同与资源浪费。更重要的是,诸如哲学、古文字学、基础物理、人类学等学科虽然“冷门”,却有真正的公共价值、学术深度和文明意义,甚至关乎文明传承与国家基础,这些学科亟须在结构优化中获得制度性保障。结构优化不能在政治风口与市场热度之间反复摇摆,而应建立在教育系统的长期主义与多样性容纳能力之上。
当前,改革体系日益依赖技术治理与数字化手段,如周期性合格评估、水平评估、成果抽检、实践成果认定等。其出发点在于提升透明度与规范性,但也存在一个悖论——当所有高校都以“通过评估”或“获得更高评级”为目标组织教学、配置资源时,改革的实质将变成“迎合指标”而非结构自觉。我们担忧,指标体系的精密化若未同步释放制度弹性与信任空间,改革将滑向“行政计划的精细升级”,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组织自主。
改革的力量最终还应转向高校自身。当前,不少高校仍缺乏动态调整意识,专业结构靠项目叠加,撤点靠政策推动,缺乏面向未来的自我革新能力。要摆脱这种路径依赖,必须推动高校建立基于市场信号、就业反馈与教学绩效的常态机制,使教学、科研、招生、社会服务形成内在循环,让结构优化真正动起来、活起来。
早在10多年前,学科与专业的动态调整政策其实就已经建立起框架,部分高校也已形成成熟机制,将专业优化纳入发展规划与质量体系。但也有相当多的高校选择回避矛盾,宁可暂停招生也不触碰结构问题。这种“冻结而非重组”的应对策略虽可保持短期稳态,却延缓改革进程,甚至加剧高校间的发展分化。
因此,改革推进应区别对待——机制健全者应鼓励其保持节奏,避免“清仓式”重启;尚未建立有效机制的高校,应重点构建监测、预警、评估、决策、调整的完整链条。改革不在于统一动作,而在于分类推进、成熟节奏、制度建设。
我们支持改革让高校更具市场洞察与调适能力,但也希望改革能体现对教育系统差异性的深刻理解。高校学科结构不是静态平面,而是一个复杂生态。有的学科市场导向强,应适度竞争;有的学科公共性强,应制度保护。结构优化应是一次有战略耐心的演化,而非粗暴整编的动员。一场真正成功的改革最终不在于撤并了多少点,而在于是否唤醒了高校内生性的结构治理能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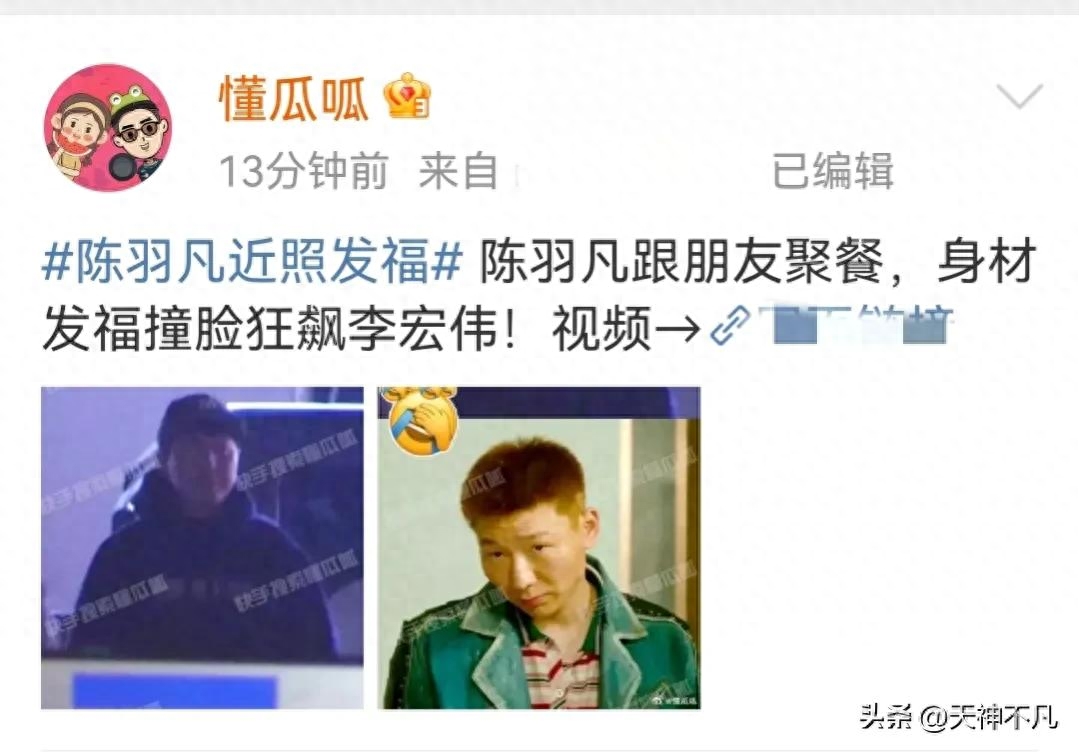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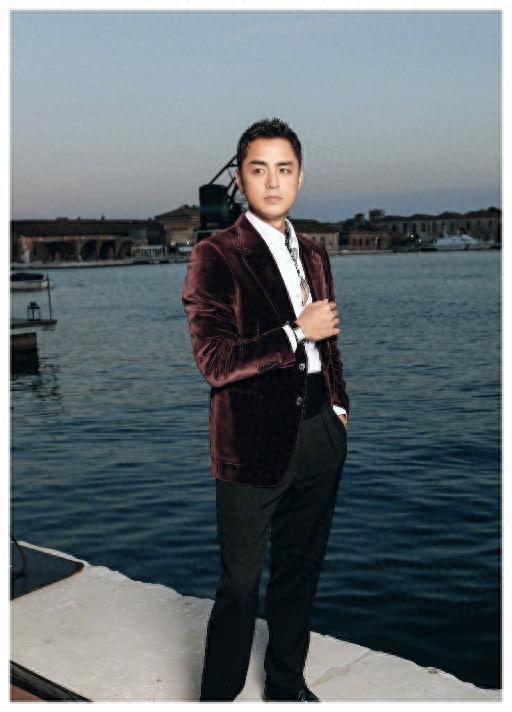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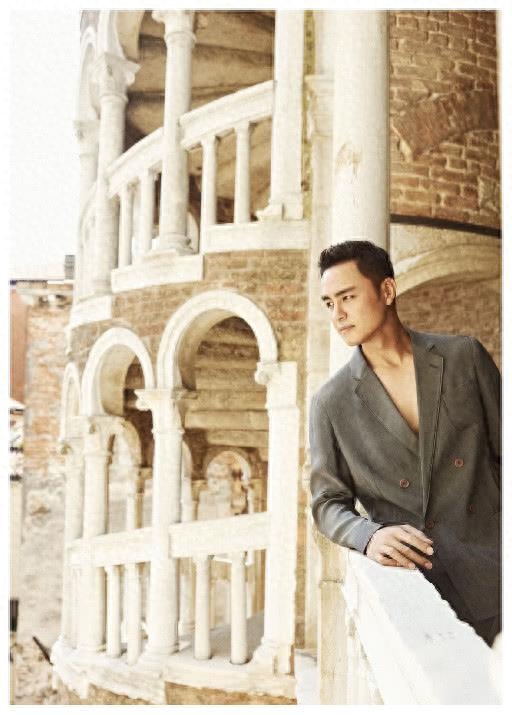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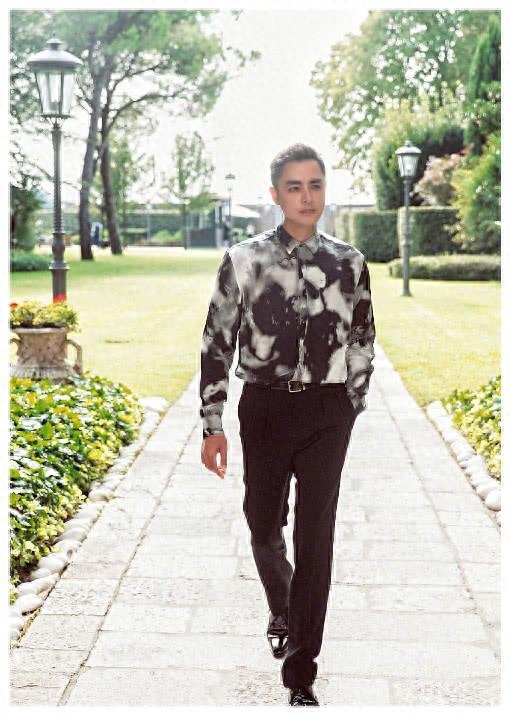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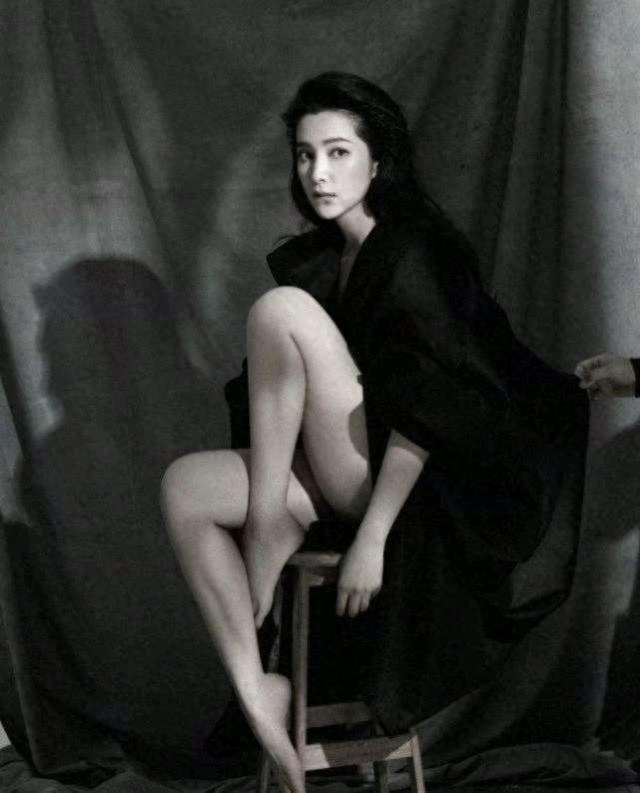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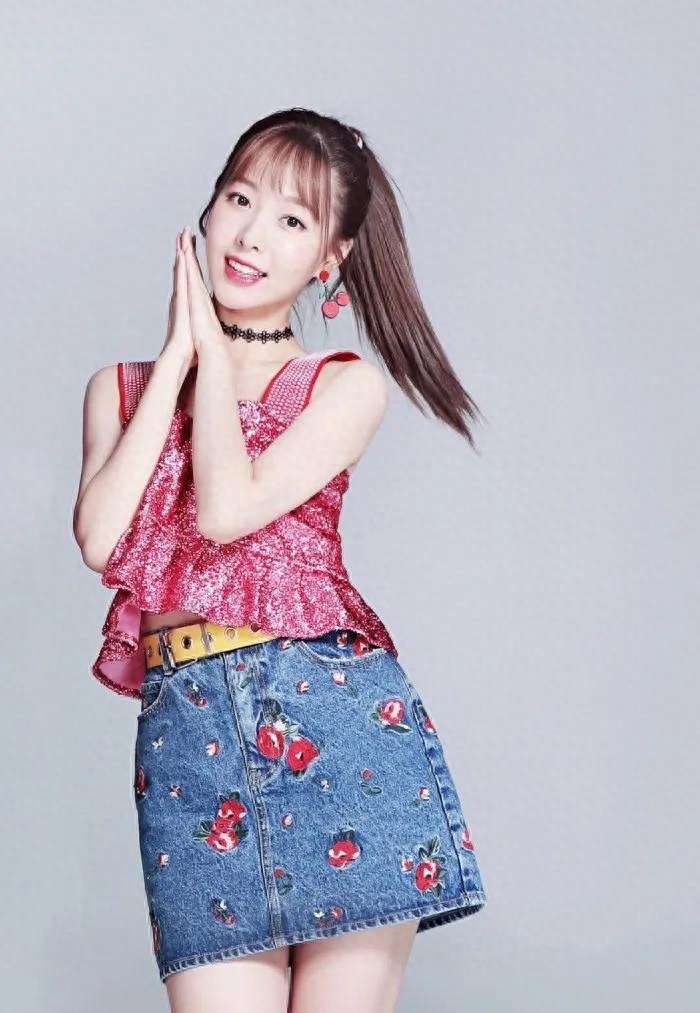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0 条